看台如炸开的火药桶,声浪几乎要掀翻球馆穹顶,记分牌猩红地闪烁着,第四节剩三分钟,我们落后九分,教练喊了暂停,汗珠顺着他灰白的鬓角滚落,战术板被敲得“梆梆”响,但每个人眼底都浮着一层冰,目光游移,几乎是不约而同地,落在我身上,那个被钉在板凳末端的、本不该出现在这场绞肉机般季后赛的身影——我,阿克。
耳机里循环的肖邦《雨滴》,总在某个小节被我笨拙地弹错,母亲说,那预示着心乱了,就像现在,胸腔里那面鼓,敲得毫无章法,镁光灯太亮,像手术台上的无影灯,要把我这具失败的躯体照个对穿,我想起一周前的地方小报标题:“陨落之子:从城市英雄到累赘”,他们说,我膝盖里取出的不光有碎骨,还有胆气;说那记葬送去年总决赛的离谱失误,是我篮球智商永恒的污点。
可我更忘不了的,是昨夜在“莱克老爹披萨店”后巷,油腻的霓虹灯牌下,老爹用沾满面粉的手拍了拍我的肩,什么都没说,只递给我一块边缘烤得焦脆的香肠披萨,隔壁理发店的雷兹叔叔晃出来,咧开缺颗门牙的嘴:“小子,这城市的地基,是用钢铁厂的煤渣和老工人们的倔脾气打的,塌不了。”他们没提篮球,没提救赎,但我尝出来了,那披萨的咸味里,掺着这座以工业衰败闻名、却从未低下过头颅的城市的味道,我是阿克,阿克隆的儿子。

哨响,我被推上场,地板滚烫,九分的分差像东非大裂谷横在眼前,第一个回合,我漏了人,对方后卫像条泥鳅从我身边滑过,轻松上篮,嘘声,针尖般刺来,时间还剩两分十五秒,八分差距,球意外地滚到我脚边,那一秒,世界失声,我看见篮筐,看见去年夏天那只在指尖绝望旋转后滑出的球,看见母亲钢琴上停滞的乐谱。
不,不是这样。
身体先于思考启动,一次笨拙却坚定的跨步,倚住补防的巨人,不是抛投,是将全身的重量、破碎的自信、巷子里披萨的油香、老爹手掌的温度,全部拧成一股决绝的力,向那该死的篮筐砸去!
球进,加罚。
站上罚球线,汗水蛰疼眼睛,我拍了两下球,皮革的触感从未如此真实,出手,一道平直的轨迹,网窝甚至没多颤动一下,还剩五分。
防守,我像疯狗般缠上对方的箭头人物,一次、两次,用伤痕累累的膝盖去顶,去预判,抢断!球权交换,队友突破分球,三分线外,我接球,没有丝毫犹豫,起跳,出手,篮球划过穹顶,带着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呼吸、每一声叹息、每一个不肯熄灭的期望,坠落。
刷——!追平!
加时赛,我已感觉不到双腿,只有燃烧的意志,一次关键的篮板,一记贯穿全场、精准找到空位队友的长传,以及最后十一秒,那记用尽最后气力、扭曲着身体打成的“2+1”,球进的那一刻,我知道,我们拿下了,不是靠我一个人,但我这粒几乎被弃用的火星,终究溅入了油箱。
终场哨响,我瘫倒在地,大口呼吸,队友们扑上来,叠罗汉的重量几乎让我窒息,但我看见了,看台上,雷兹叔叔举着一块不知从哪里搞来的硬纸板,上面用粗犷的马克笔写着:“欢迎回家,小子。”
更衣室手机震动,母亲发来一段视频,家里那架老钢琴前,她弹完了整首《雨滴》,流畅,圆满,附言:“你走时落下的音符,妈妈替你补上了。”

走在午夜空旷的球员通道,回声很大,救赎是什么?不是镁光灯下独舞的英雄史诗,或许,它只是一块焦脆的披萨,一声缺牙的鼓励,一首终于弹完的曲子和一粒拒绝熄灭、最终点燃整片荒原的卑微星火。
我是阿克,今夜,我和我的城市,一起从瓦砾中,站了起来,而这,仅仅是个开始。
版权声明
本文仅代表开云体育观点立场。
本文系作者开元官方发表,未经许可,不得转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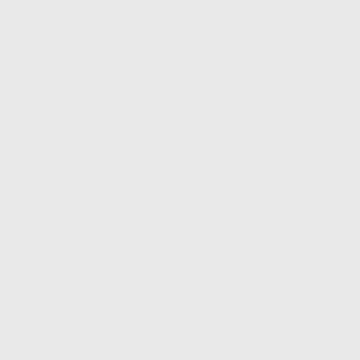
评论列表
发表评论